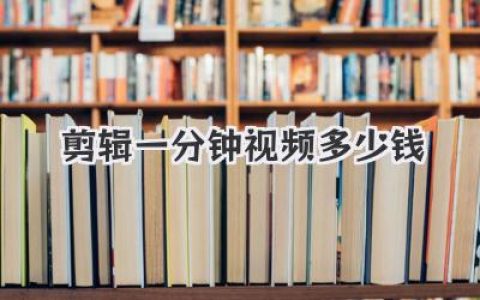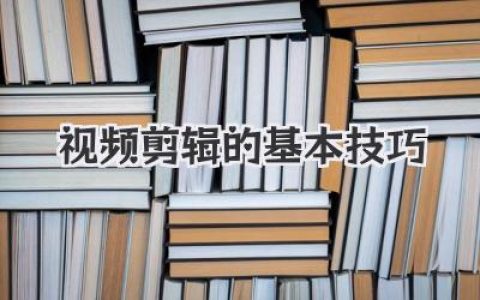聊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绕不开它的美术,它的服化道,但说真的,在我心里封神的,是那神乎其技的长安十二时辰剪辑。这玩意儿,它不是锦上添花,它就是这部剧的骨架和灵魂,是那只看不见的手,掐着你的脖子,拖着你跟张小敬一起,跑完这要命的十二个时辰。
你还记得吗?开篇那段长镜头,一镜到底,从西市的喧闹,穿过人群,掠过摊贩,最后落在一个不起眼的胡人身上。当时觉得,哇,牛。但现在回看,那只是开胃菜。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,是当叙事展开后,那种被时间追着打的压迫感。这压迫感怎么来的?全靠剪辑。

剧里那个不断出现的水漏、日晷,还有报时鼓,它们不是简单的计时工具。每一次“咚”的一声鼓响,镜头都会给你一个凌厉的切换。可能是从张小敬在地下城里的一场恶斗,瞬间切到靖安司里李必紧锁的眉头;也可能是从歌姬许鹤子华丽的舞台,骤然跳到某个阴暗角落里正在点燃的引信。这种切换,干脆利落,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它在不断地提醒你,提醒所有人:时间不多了。这种感觉,就像一场漫长的、不见终点的溺水,你刚探出头想喘口气,就被剪辑师一巴掌又按了下去。
我敢说,长安十二时辰剪辑最绝的一点,就是它对双线乃至多线叙事的掌控力。一条线,是张小敬这条“腿”,在长安城的肌理中横冲直撞,用最原始的暴力和直觉追查狼卫。他的世界是动态的,是混乱的,是血和土的味道。另一条线,是李必这个“脑”,在靖安司运筹帷幄,调度资源,分析情报。他的世界是相对静态的,是紧张的,是沙盘和烛火的味道。
剪辑师做的,就是把这两条线拧成一股麻绳。你看张小敬在底下巷战里杀得血肉模糊,镜头一转,切给靖安司里李必紧锁的眉头和沙盘上被挪动的一枚棋子,这中间没有一句废话,但那种焦灼感,那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,简直要把屏幕都烧穿了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平行剪辑了,这是情绪的共振,是信息的互补。张小敬的行动是“果”,而李必的决策是“因”,剪辑把因果关系打碎了,再重新拼接,让你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惨烈和决策的艰难。这种处理方式,高级得令人拍案叫绝。
再说说动作戏。这部剧的打斗,为什么看得那么爽,那么真实?镜头晃,跟拍快,这些都是基础。但核心还是剪辑的节奏。它不是一味地快。你看张小敬追击的时候,会有大量快速、破碎的镜头拼接,让你感受到那种奔跑中的眩晕和急迫。但关键时刻,比如刀锋相交的一瞬间,它会突然给你一个慢放,或者一个特写,让你看清刀刃上的寒光,或者溅起的血珠。这种一张一弛,就像呼吸,让整个动作场面有了生命力。它不是在展示套路,它是在让你体验一场生死搏杀。
而且,这部剧的剪辑特别“不老实”,它总是在挑战你的观影习惯。它敢于在信息量极大的时候,用非常快的节奏去推进。靖安司里,一大堆人名、官职、地名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,镜头在不同人的脸上飞速切换,你根本来不及细想,就被裹挟着往前走。这在别的剧里可能是灾难,但在这里,却恰如其分地营造出了那种危在旦夕、分秒必争的真实氛围。你就像一个刚被扔进靖安司的小吏,懵,但是必须跟上。这种沉浸感,是靠剧本写不出来的,是剪辑师一帧一帧“剪”出来的。
我甚至觉得,长安十二时辰剪辑本身,就是一种独特的语言。它有自己的语法和词汇。那些碎片化的闪回,不是为了拖时间,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,给你一把理解人物动机的钥匙。比如对第八团的回忆,它不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,而是在张小敬最孤独、最绝望的时候,像刀子一样扎进来,让你瞬间明白他为何而战。这些记忆的碎片,通过剪辑,和现实的残酷时间线交织在一起,塑造了一个无比立体的“十年西域兵,九年不良帅”。
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个“长安反恐二十四小时”的故事。它的野心更大。通过剪辑,它把一个盛世的华美与阴暗、一个英雄的挣扎与坚守、一个天才的理想与现实,全都浓缩在这短短的十二个时辰里。每一次镜头的切换,都是一次选择,都是一种态度。它让你看到的,不只是一个故事,更是一个鲜活的、正在呼吸的大唐。
所以,当我们赞美这部剧的时候,请一定给它的剪辑师留一个大大的位置。是他们,用手术刀般精准的切割,赋予了时间以重量,赋予了叙事以心跳。这已经不是技术了,这是艺术。一种让你的肾上腺素和泪腺同时失控的,了不起的艺术。
原创文章,作者:剪辑研究所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douyin766.com/18248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