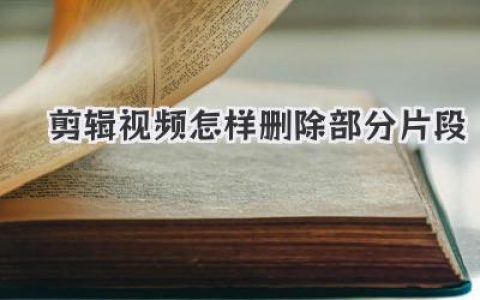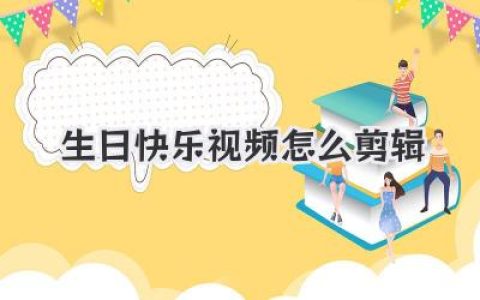这问题问得,就好像在问一个厨子:“菜是怎么做菜的?”。太大了,也太小了。大到可以写几本书,小到可能就是鼠标的一次点击。但你要真想知道,行,我掰开揉碎了,用大白话给你聊聊,剪辑这活儿,到底是在捣鼓些什么。
首先,你得忘了那些酷炫的软件界面、快捷键。那些是“器”,是工具,不是“道”,不是灵魂。剪辑怎样剪辑的? 核心,永远是讲一个好故事,哪怕这个故事只有15秒。
一切的开始,是一场灾难。
你面对的,是几个小时,甚至几十上百个小时的素材。它们杂乱无章,堆在你的硬盘里,像一堆未经筛选的矿石。有导演喊“action”前的尴尬沉默,有演员NG时的一句脏话,有场工乱入的某个瞬间……什么都有。这时候的你,不是剪辑师,是个垃圾佬,是个侦探,是个考古学家。你的第一步,根本不是“剪”,而是“看”,是阅片。
这个过程极其枯燥,也极其重要。你得耐着性子,把所有东西都过一遍。在脑子里给它们打上标签:“这条情绪对了”、“这个眼神能用”、“这句台词是废话”、“哦!这个意外的镜头或许是个惊喜”。这个阶段,你在跟素材谈恋爱,了解它的脾气,它的闪光点,它的缺陷。你脑子里慢慢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,一个故事的骨架。
然后,真正的战斗开始了——粗剪。
粗剪,说白了,就是搭骨架。别管什么精细的转场,别管什么声音的细节。就是一个字:“杀”。把你在阅片时记下的那些“能用”的片段,按照你脑子里故事的顺序,毫不留情地扔到时间线上。咔咔咔,砍掉开头,砍掉结尾,只留下最核心的部分。这时候的时间线,看起来就像个车祸现场,到处是生硬的切口,声音断断续续,画面跳来跳去。很丑,真的。但没关系,因为一个故事的雏形,第一次,活了过来。它有了开头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尾。尽管它还站不稳,但它有了心跳。这,就是叙事结构的建立。
接下来,才是见真功夫的时刻——精剪。
如果说粗剪是搭骨架,精剪就是长血肉。你开始处理每一个“切点”。这个画面,是多留一帧,还是少留一帧?观众的情绪就在这一帧之间,可能就从紧张变成了泄气。你开始玩弄节奏。
什么是节奏?它就是剪辑的呼吸。一段激烈的追逐戏,可能需要零点几秒的快速切换,画面、音效、音乐,像暴风雨一样砸向观众,让他们喘不过气。而一段深情的告白,你可能会用一个长镜头,让时间变慢,让观众沉浸在角色的眼神里,去感受那份情绪的流动。这就是剪辑师的魔法,通过控制时间,来控制观众的情绪曲线。
这里面有很多小伎俩。比如我们常说的J-cut和L-cut。说白了,就是“声画分离”。你想想看,画面还在上一个场景,下一个场景的声音却先进来了,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的好奇心勾起来了?或者,人物已经说完话走出了画面,但他的声音还在回响,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,不就出来了吗?这些都是在给故事的血肉,注入灵魂。你不再是简单地拼接,你是在“编织”。
故事的血肉丰满了,但它还不够“好看”,不够“好听”。于是,就到了后面两个重要的环节。
一个是声音。我跟你说,声音,在很多时候,比画面还重要。它直接作用于你的潜意识。你以为你在看电影,其实你更是在“听”电影。一个完整的声景,至少包括:人物的对白、环境的底噪声(风声、雨声、街道的嘈杂声)、特殊音效(关门声、枪声、心跳声),以及最重要的——音乐。你试试看,把一部恐怖片的背景音乐关掉,恐怖感至少减掉八成。声音设计,是给整个片子铺上一层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情绪地毯。
另一个,是调色。调色不是简单地把画面调亮点、调得饱和一点。不。调色是在“画”情绪。你看王家卫的电影,那种昏黄、潮湿的色调,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拉进了那个暧昧、疏离的氛围里?你看那些科幻大片,那种冷峻的蓝绿色调,是不是科技感和未来感就出来了?颜色,本身就是一种语言。温暖的色调可以传递幸福和怀旧,冷色调可以表达孤独和恐惧。调色,是剪辑师递给观众的最后一副“情绪眼镜”。
所以,回到最初的问题,剪辑怎样剪辑的?
它不是一个线性的、机械的流程。它是一场混乱的创造,一场与素材的博弈,一场在时间线上进行的心理游戏。
它是在一堆废墟里,看到一座宫殿的潜力。
它是在几十个NG的镜头里,找到一个最真实的眼神。
它是在沉默的画面里,听到故事的心跳。
它需要你像个冷酷的杀手,毫不犹豫地剪掉那些拖沓的、无用的部分,哪怕那是导演最喜欢的一个镜头。也需要你像个多情的诗人,为了那一帧画面的情绪,跟自己反复拉扯。
这活儿,没有绝对的对错。有时候,一个“错误”的剪辑,一个意外的跳切,反而成了神来之笔。最终,你追求的,是一种“感觉”,一种“手感”。当整个片子看下来,行云流水,情绪一气呵成,观众跟着你预设的节奏哭、笑、紧张、释然……你就成功了。
那个瞬间,你不是在剪辑,你是在施法。而那个被你创造出来的作品,它有了自己的生命。这,大概就是剪辑这门手艺,最迷人的地方。
原创文章,作者:剪辑研究所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douyin766.com/181906.html